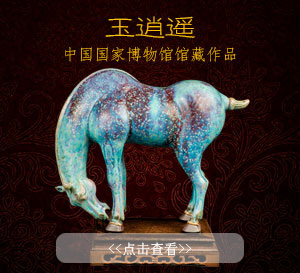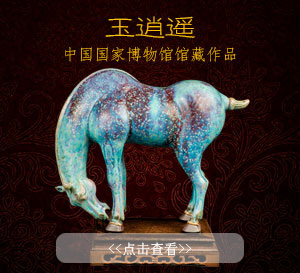2019年4月,《中国文物报》以几乎整版的篇幅,刊发了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钧瓷烧制技艺代表性传承人、中国陶瓷艺术大师苗长强的采访。在该文中,苗长强围绕历史上的唐钧花瓷与后来的钧瓷的关系、现代钧瓷工艺借鉴古代钧官窑工艺并有所突破、古代钧瓷工艺与现代钧瓷工艺的异同、现在钧窑的传承发展情况等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中国陶瓷艺术大师苗长强
5月,苗长强将钧官窑标本和其创作的“宋釉今烧”作品标本在中科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进行了化验分析,结果显示釉料成分基本一致。同月,苗锡锦、苗长强“宋釉今烧”成果学术研讨暨专家认证会在上海召开,21位古陶瓷专家、中国各大窑系的扛鼎艺术大师和“大国工匠”共同出席、研讨认证,认为他们烧制的宋代典型钧瓷《鸡心罐》《鼓钉洗》等与钧官窑古瓷釉色接近,神韵俱佳。
何为“宋釉今烧”?为何要进行“宋釉今烧”?其技术难点又在哪里?不久前,在禹州市神垕镇苗家钧窑,苗长强谈及了其与父亲苗锡锦的古瓷情结。
苗氏父子难舍的古瓷情结
“小小的一片瓷承载着华夏漫长的文明史,若被一个普通人发现可能会不屑一顾,若是好玩之人可能会用它打水漂儿,若是被一位古陶瓷爱好者发现,肯定会把它轻轻地捡起来,擦去上面的浮灰,然后刷洗干净,视如珍宝。”苗长强说,一片古瓷片可以呈现非常多的内容和细节,其父苗锡锦的钧瓷情结,就起源于那些埋藏土中的古瓷片。

苗长强作品《鸡心罐》
作为钧瓷界的“活化石”,苗锡锦是对钧瓷文化的挖掘、传承和弘扬作出重大贡献的开拓性人物。钧瓷“始于唐,盛于宋”,这在如今都是常识。但为何说钧瓷“始于唐”,苗锡锦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一个重大发现为这个问题的解答提供了思路。1977年冬,苗锡锦在神垕镇钧窑集中产区下白峪村赵家门的倒流河处发现了沉睡千年的唐代黑釉花瓷古窑遗址,出土的有窑炉、泥池、窑具、残器等。他当即把标本送往北京故宫博物院,经古陶瓷专家冯先铭和李知晏鉴定,确定为唐代遗存(标本现在北京故宫博物院保存)。这一古窑址的发现,为研究中国陶瓷发展史提供了极其宝贵的资料。
“为了弄清楚宋代钧瓷的‘前世今生’,对古窑址的发掘考察是我们梦寐以求的事情。自从1977年冬在神垕下白峪发现唐黑釉花瓷至今,我们对黑釉花瓷的研究从未停止过,把从下白峪古窑址得到的这些标本送到了北京故宫博物院中国古陶瓷学会,经时任中国古陶瓷学会会长冯先明、副会长李志宴等的鉴定,确认无疑是唐代所制。2005年,山东省硅酸盐设计研究院高级工程师刘凯民采用现代科技手段测试和分析,论证了唐代花瓷釉与宋元钧窑系釉等分相乳光釉的源流传承关系。”苗长强说,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弄清钧瓷的历史发展脉络,靠的是对古窑址、古瓷片等的研究。
钧官窑是钧窑的一面旗帜
“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这是陈寅恪先生曾说过的一句话。苗锡锦常常引用这句话。钧瓷作为宋代五大名瓷之一,代表了当时的文化发展潮流和时代审美情趣,也对后世钧瓷艺术的传承和弘扬产生了深远影响。至今,在钧瓷艺术不断发展新器型、新釉色的同时,可能每一个“钧瓷人”都对宋代钧瓷保持着敬仰和推崇之情。

苗长强作品《东方红鼎》
“我的父亲经常对我说,钧官窑是钧窑的一面旗帜,我们一定要把它发扬光大。”苗长强说,这句话对他的钧瓷艺术之路产生了深远影响。“位于禹州市老城区的宋代钧官窑址,是北宋时为皇室烧制钧瓷贡器的官办大型窑场。该窑场所烧制钧瓷器皿,无论是从釉色方面还是造型方面看,都代表着钧瓷艺术鼎盛时期的最高工艺水平。珍藏于国内外各博物馆的少量宋代传世钧瓷及该遗址近几年发掘出土的钧瓷残片标本,精美绝伦,在国内外都享有很高的声誉。”苗长强说。
“1973年,对宋代钧官窑址中的一处制瓷作坊残地进行抢救性发掘时,清理出了疑似澄滤后的钧瓷釉料土层。这次发现当即引起我父亲的重视,他立刻拿到当时工作的地方国营钧瓷厂化验,结果显示这些土料成分符合钧瓷釉料高硅低铝的基本要求。父亲认为这种原料极有可能是我们朝夕期盼、能够解开宋代钧釉之谜的釉原料。由于当时的国营钧瓷厂化验室设备条件有限,不可能对土料作出全面分析,他们又将部分土料标本寄往山东省硅酸盐研究设计院,请该院著名的硅酸盐研究专家刘凯民对这些土料进行化验分析,发现该土料含氧化硅 77.2%、氧化铝9.07%。两地化验结果虽然在氧化铝含量上微有差异,但在高硅低铝的认定上是一致的。据此可以初步肯定,这些土料就是宋代钧官窑当年使用而被遗留下来的釉原料,而且是经过淘洗、澄滤、沉淀等工序之后的纯净釉料。”苗长强说。
苗长强说,为了进一步揭开这批出土釉料的奥秘,他和父亲对此釉料进行烧制观察,第一次试烧后,烧成结果令人大失所望,成品暗淡无光,色调难以用语言形容。在长达数年的岁月里,经历了无数次的失败,父子二人最终用出土釉料成功烧制出了堪与宋官窑器皿釉色相媲美的天青釉、月白釉和玫瑰紫釉,作品受到陶瓷泰斗耿宝昌先生和中国古陶瓷学会原会长王莉英的高度评价,被称为“宋釉今烧”,使得千年前的珍品得以还原。
“根据《硅酸盐学报》2008年6月第三十六卷第6期《三种釉色官钧窑瓷和现代高档钧瓷的中子活化分析》一文,李国霞、孙洪巍、孙新民、赵青云等14位学者的研究报告认为我们当时烧制的复烧品最接近钧官窑钧瓷的成分数据。为了能更清楚地对比钧官窑钧瓷标本的化学组成,不久前我们又找到当今科技水平最高的中科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将钧官窑标本和我们的‘宋釉今烧’标本进行了化验分析,结果基本一致。”苗长强说。

苗长强作品《福禄尊》
钧釉的奇妙效果与本地原料的性质及微量元素、地理环境都有一定的关系。从艺术效果到成分构成,苗长强与父亲烧制的“宋釉今烧”作品,完美再现了宋钧神韵。苗氏父子在钧官窑釉料和釉色研究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在钧窑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重要意义。
钧瓷发展要根植传统面向现代
什么是好的钧瓷?好的钧瓷能够跨越时空,从宋代到现代,甚至以后也传承不衰;好的钧瓷能够跨越地域,影响着从神垕到禹州,再到中国甚至世界的审美取向。古人有古人的追求,今人有今人的审美。既不能以传承为理由因循守旧,也不能以创新为借口异想天开。

苗长强作品《长城鼎》
“父亲曾说,创新不离宗,仿古不拟古。我的钧瓷创作一直受这句话影响。”苗长强说,在钧瓷新釉色的开发和新造型的设计上,他一直坚持这一原则。在苗长强看来,端庄大方、古朴典雅是传统钧瓷的魅力所在。在器型的创新上,苗长强一直坚持这一特色。他的作品《长城鼎》《小口尊》等皆是如此,大气、浑厚、庄重、震撼。“我们不一定要一直模仿古人的作品,只要创新的器型能够体现传统器型的特点,就是好作品。”苗长强说,“钧瓷在每一个发展时期都有自己的特点,由于追求不一样,自然产生了不同的风格。钧瓷的器型和釉色发展到今天,说令人眼花缭乱并不夸张。但在纷繁复杂之中,我们应该把握一条主线,不管钧瓷如何发展,我们都应该将钧瓷的特质传承下去。”
“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不同朝代有着不同的艺术风格。审美和用途的不同,自然会产生各式各样的作品。我们‘钧瓷人’应该始终坚持自身特色。钧瓷之美,美在器型,更美在釉色。一件钧瓷作品的造型一定要体现出釉色之美,要用一定的釉面来展现釉色。因此,钧瓷的造型一定要繁简有度。”苗长强说。
追寻着千年前的辉煌,以宋代钧瓷为蓝本,苗长强探索着钧瓷艺术的更多可能。